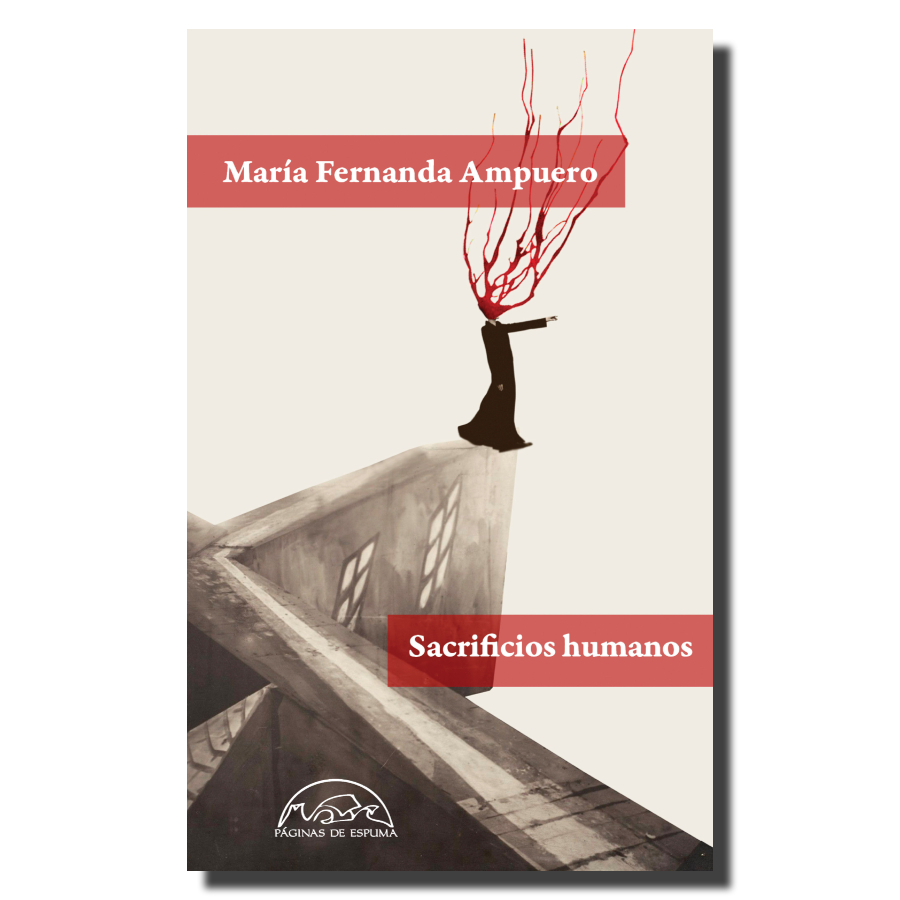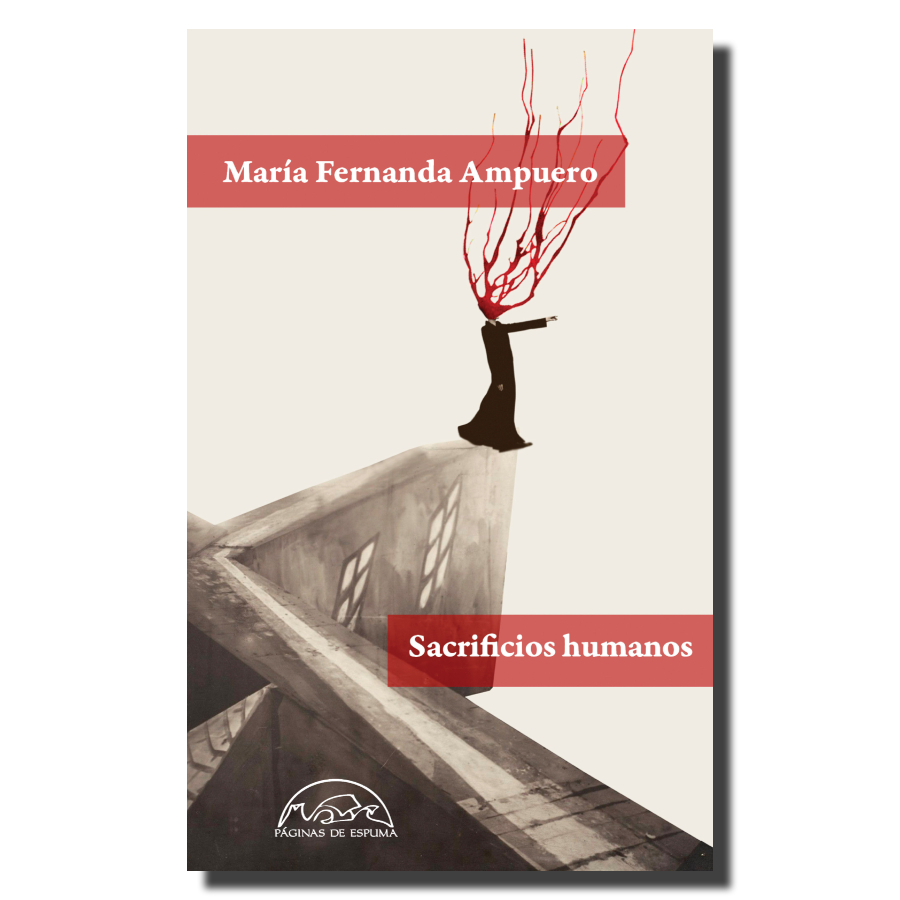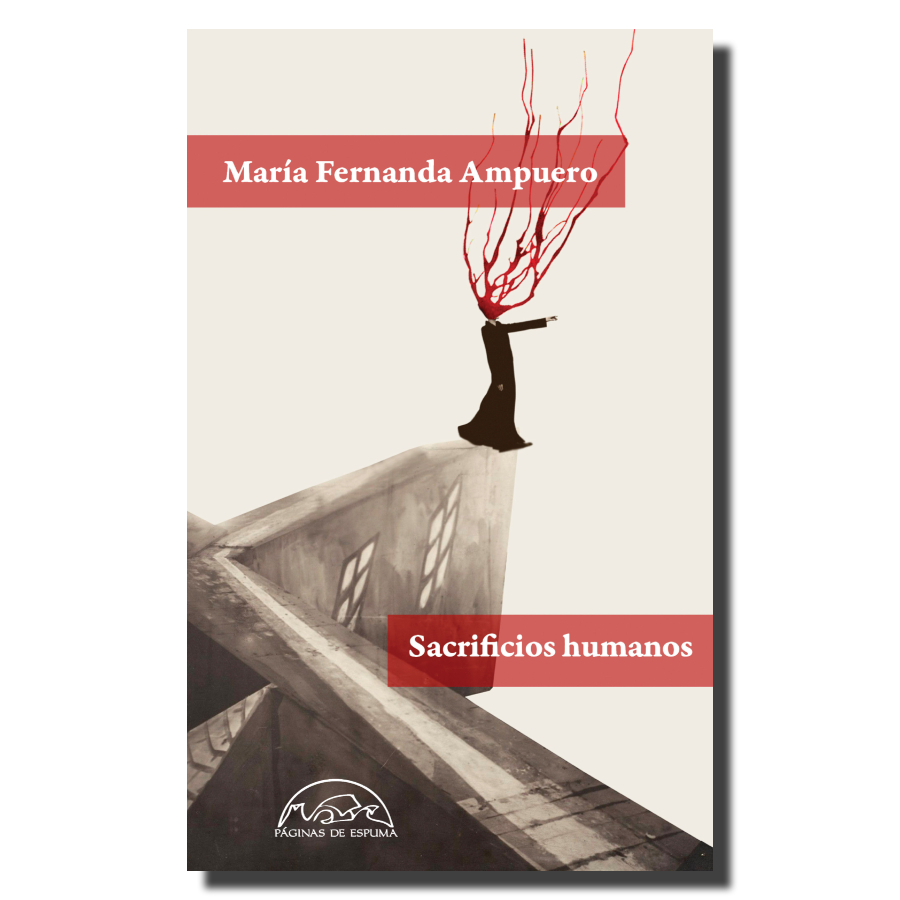
Sacrificios humanos
by María Fernanda Ampuero
《人祭》是厄瓜多尔作家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安普埃罗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,2023年被译成英文出版。此书由十二个短篇故事组成,关注性别、移民、社会不公、生态等议题。《人祭》入选
《纽约时报》2023年度最佳恐怖小说
书单,并被誉为 “
文学界的女权主义死亡金属专辑
”。
今天推送的是其中一则仅有三千多字的超短篇,故事讲述了一个拉丁裔年轻女性移民在美国的生活。她的经历也可能是每个女人的经历,是每个外来者的经历。

封面图:《子宫和卵巢死亡金属头骨》
Jennifer O'Toole
著/玛丽亚·费尔南达·安普埃罗
安
吉莉塔说她要给我介绍个真命天子,我说:“又来?”她说:“对,他很帅,很适合你。”我画了猫眼眼线,涂了闪亮的口红,因为我至少要从中得到一些热吻。那
家伙是个鬼佬,我喜欢鬼佬。是的。我喜欢他们闻起来像香皂,像洗衣粉,没有别的味儿。我喜欢他们洁白完美的牙齿。我喜欢他们傻乎乎的样子。我喜欢他们掏钱
的时候不假思索。我喜欢他们在床上表现得那么孩子气,满怀感激。他们大喊哦上帝哦上帝,他们射出的液体没有一点气味,或者有一点像香皂,像洗衣粉。我要睡
到这个鬼佬。我穿上一件低胸紧身上衣,穿上特意订购的内衣,它能把我平坦的屁股提得又圆又翘。
我
们去了一个墨西哥人常去的地方,因为这些鬼佬不管嘴上怎么说,心里总认为我们都是墨西哥人,认为我们在这种地方有回家的感觉,认为墨西哥菜能让我们欲火焚
身。来吧,性感辣妞。三扎玛格丽特喝下肚,我们开始跳舞。这个鬼佬,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害羞。那双恶魔般的绿眼睛看起来超变态。他把手伸进我的内衣里,
手指滑进臀缝之间。哦,这个鬼佬。我爱死了。
他
长得像童话里的王子:棕色头发,白色皮肤,身材高大,肌肉发达。更重要的是,他很有侵略性。我要是不把他的手拿走,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扒得一干二净。
周围的人已经被我们震惊了,一位墨西哥女士不停在胸口划十字。我们甚至没等到回家,一上车就干起来。他的力量、尺寸、体型和技巧多么惊人。哦,这个鬼佬。
他毕竟是个鬼佬,他还是要喊yes,yes,yes,只喊yes和哦上帝。我们都高潮了,几乎在快感中昏厥。我们沉醉其中,看着对方,突然都大笑起来。就
像一对白痴。也许这家伙真像安吉莉塔说的那样,是我的真命天子。
我
们去他家继续。我们干得像动物一样,不停不歇,高声尖叫,从周六晚上干到周日早上。他捅我,戳我,舔我,吃我,喝我,吞我,打我,直到我快活得失去意识。
周日晚上我回到家,照照镜子:嘴唇肿了,乳头被咬破了,几乎是紫色的,我的脖子上布满了吻痕。我笑得像个十五岁的少女。我爱上了这个鬼佬炮神。但这只是打
炮而已,洛雷娜,他不会打电话给你了。我几乎走不了路,我的下体在灼烧。我爬上床,昏睡过去。
周
一下班后,我跟安吉莉塔通电话。她尴尬得又笑又叫。“荡妇!”她对我说,“洛雷娜你真是个荡妇。”她的室友把她轰出了公寓,因为她太吵了。她说约翰询问我
的情况,他想再次约我出去,他说他非常喜欢我。现在换我尖叫了。我叫得那么响,像个疯女人,直到邻居敲墙,威胁要报警。凶什么凶,你们这些混蛋,少来烦
我。
在
几个朋友的见证下,约翰和我结婚了。他的家人不太接受他迎娶一个他们认都不认识的拉丁裔女人,一个美甲师,一个移民,上帝啊,但他一点也不在乎。我头上戴
着粉色的鲜花,他穿着蓝色的军装。我看到他站在圣坛前等我,那么鬼佬,那么高大,那么英俊,我爱死他了。我的心怦怦直跳。像我这样挨家挨户推销化妆品、给
富婆做指甲的女孩,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的梦想会实现。
世上没有哪个人能像约翰那样让我充满欲望。一种以饥渴为食的饥渴。性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,我们不关心其他任何人任何事。我们不看电视,不出门,也不见朋友。我们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做爱。从没有哪个男人能比得上我的鬼佬,我的约翰,一头猛兽,我的长着几把的美国梦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女人都有这种感觉:干完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爱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。就像我可以伸出手触摸它,紧紧地拥抱它,仿佛它是一个会飘走的氦气球。有时候我想象我从高处俯视我们俩,看见两人干得大汗淋漓闪闪发光。我喜欢我的身体靠在他身边的样子。
我们永远不能没有啤酒。就好像百威是我们的赞助商。只要啤酒喝完了,约翰就会发狂。他脸涨得通红,责备我说:你从来不为我着想。他抓起车钥匙,出去再买几打罐装的。有足球比赛时,他一口气能喝下二十罐。
女人不会某天早上一醒来就知道从这天起她的生活将掉进粪坑。接下来的无数天中的第一天。如果我们能提前知道,如果那一天就像日历上用红色标出的圣徒日,我们就可以做好准备,远离它,保护自己。日夜交替,随着那场与时间一样古老的舞蹈继续跳下去,黑暗渗入了房子。
我
在洗碗。他在喝酒。我让他慢点喝,说他一小时已经喝下去十罐了。他从沙发上站起来,把我扔到墙上,朝我啐口水。他说我是个傻逼拉丁女人,一个傻逼拉丁女人
没资格教育他该喝多少啤酒。他摇晃一罐啤酒,然后打开,喷在我刚打扫过的厨房里。泡沫覆盖了我,覆盖了一尘不染的盘子、闪闪发光的餐刀,锅碗瓢盆上反射着
他的怒火和我的恐惧。
如同一个在房子里作祟的恶灵,跟着你从卫生间到卧室再到餐厅,那个已不是我所爱的男人四处漂浮,像一个鬼,一个魔鬼。他总是阴魂不散。
每
次我说话他都模仿我,用的声音是有精神问题的人的声音。“你就是这样说话的,”他大笑,“你说话就像个白痴。”我说有本事你也说外语,当一天外国人试试。
他狠狠扇了我一巴掌,打得我晕头转向。他用巨大的手掌掐住我的脖子,他说他永远不会变成外国人,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是瘪三。他说如果我再顶嘴,他会把我
打到只能坐轮椅。
我
不再说话了。每次我要对他说些什么,我都会在脑子里练习十遍。当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时,听起来就像语言教师的示范录音。他笑得更厉害了。“你太给我丢人
了,”他说,“你就像一只被驯服的动物,你真难看,丑八怪,我为什么要娶你。”他告诉我,如果不是因为他,我就会像这个国家的其他拉丁妓女一样站街。“我
要让你被驱逐出境,你是什么东西。垃圾。”
在
客厅对我说出这些话的人夜里要睡在我的床上。十罐、十二罐、二十罐啤酒下肚,他想做的只是伤害我。一个曾在朋友和上帝的见证下发誓说爱他的女人,为什么在
身体被丈夫撕裂之后还要擦洗他们婚床上的血迹。一个坠入爱河的女人为什么需要给私处的伤口消毒。一个女人为什么会在丈夫上床时怕得哭出来。
我下班回家时,总是看到他躺在沙发上,周围都是空啤酒罐。他那张漂亮的鬼佬面孔已经变了:双眼仍是绿色的,但看起来精神错乱;如果你在黑暗小巷里遇到他,那张脸会让你害怕。我的厨房就是黑暗小巷,而我的袭击者戴着一枚刻有我名字的戒指。
我
不跟任何人说任何一句话。我不想让他们讨厌约翰,也不想让他们同情我。我不想离婚,因为他们总是告诉我,离婚的女人是罪人。我也不想让家人发现我是那种我
们都听说过很多次的女人——她们忍受丈夫的酗酒和暴力殴打,因为即便挨打,即便被杀,那也仍然是她们的丈夫;她们戴着墨镜,说自己只是摔倒了;即便没人问
她们,她们也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说,我的丈夫压力很大。
没有哪个穿着荷叶边长裙、头上戴着鲜花的新娘,会想象自己将成为那种被所有人议论的女人,那种一提到名字就能让其他女士闭上眼睛直摇头的女人,那种可以用殴打、强奸、虐待、谋杀等词语来描述的女人。
约
翰在公开场合打我。我们从超市购物出来时,身边走过一个男人。他突然就发疯了,指责我跟这个陌生人调情,说我真是个荡妇,说我活该被人弄死,说他幻想一枪
打中我的肚子,看着我以慢动作倒地,趁我还没咽气时挖出我的心脏给我看,然后吃掉。停车场的其他人看着他,听着他。婊子、猪猡、恶心、肮脏,这些词语像毒
镖一样在空中飞舞。这个魁梧的男人一拳打在我脸上,把我推倒在地。没人过来帮我,没人说一句话。“上车,别等我碾在你身上,婊子。”他说。
夏
季几乎每天晚上都有足球比赛。他像往常一样烂醉,走进卧室时被各种东西绊倒。他一丝不挂,在昏暗的灯光下,我能看见他的勃起。那根我曾经崇拜的阳具,我曾
爱抚它,就好像它是我孩子的小脸蛋,我曾把它放进嘴里,从中吮吸营养。我早就不希望他进入我的身体了,我不再想要用自己的皮肤拥抱他,包裹他,直到我们在
快感中爆炸。每次他强奸我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我们初次相遇时的奇妙感受。我们曾经那么美,现在却浑身是血。
他
掀开床单,撕开我的内衣。我说:“不,不要再来了,不。”我说:“求求你了,约翰,求求你了。”然后他像电钻一样把自己塞进我体内。我不知道他持续多久,
疼痛撕裂了肉体,我就像被火穿透了一样。我离开我的身体,漂浮到高处,俯视床上的两个人,女人和男人,妻子和丈夫,被强奸者和强奸犯。我不应该看到这个,
没有人应该看到这个。
他睡着了。血腥的精液沿着我的双腿之间往下滴。我走下床,走向厨房。在黑暗中我看到了它,它像伯利恒之星一样闪耀,为我指明道路。我紧紧抓住它的柄,回到卧室。
除了这本《人祭》,我之前还介绍过安普埃罗的第一部短篇集《斗鸡》,并翻译了其中的两个超短篇。如果你喜欢她的叙事风格,可以继续阅读这两篇: